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本文所探讨的“地方性知识”并非是某种特定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我们在学习、工作、实验时都已经参与了知识的构造与辩护过程。由于我们现实所处的情境总是特定的,因此所构造和辩护的知识也总是“地方性”的。自库恩以来,随着新科学哲学、SSK的社会构造论与劳斯的文化构造论的进展,“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渐渐占据了西方科学哲学领域的主流。本文既强调“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批判意义,同时也通过实践性的参与对其开放与创新的意义做出确认。
一、何为“地方性知识”?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知识观念正处在悄悄的变革之中,“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正是这一变革的产物之一。这里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知识”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人们总以为,主张地方性知识就是否定普遍性的科学知识。这是误解。按照地方性知识的观念,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有效,这正是有待予我们考察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某种先天(a priori)原则被预先决定了的。
相对于近代的科学理念和启蒙精神来说,“地方性知识”显然具有校枉,乃至“颠覆”的意义,人们往往把这种观念与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无偏颇之处。历史上的经验论者,当其拒斥先验主义的解释,主张从有限的、局部的经验出发来构造知识时,其实都有意无意地倡导着地方性知识。然而,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尽管与经验论交叉,但并不重合。这种观念带有更浓厚的“后殖民”时代的特征。它的兴起与流行于欧美人类学界的“文化研究”、新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的科学的政治批判,以及社会构造论研究有关。这些思潮相互辉映,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发起冲击的同时,也要求对作为传统科学观念的核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作出批判。
可见,地方性知识首先具有批判的意义,其次才谈得上实质性的和建设性的意义。当今,不少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执著于后一层含义。为此,他们必须寻找到一些只能满足“local”条件的知识范例。在他们眼里,最明显的范例除了土著人的知识外还要数我国的中医。中医显然能治好疾病,但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准则,它很难称得上是科学。原因就在于中医知识是在中国传统的和本土文化的情境中生成的,因此也只能通过本土文化内部的根据来得到辩护。按此逻辑,我们似乎能得出结论,即便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也是在当时英格兰那种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之所以被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完全是由于辉格党人的政治取胜,或者殖民化的顺利进展等社会文化因素所致。这样的结论又嫌过强,知识毕竟包含不为特定情境所决定的确定的内容。本文倾向于从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地方性知识。当我们说知识并非是普遍有效的时,丝毫不意味着一切知识都是局域地有效的。
当代地方性知识的支持者们往往把这种观念溯源到亚里士多德、维科、尼采,甚至是马克思那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无疑是站在劳动的立场上来反思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但是这种非中立的立场丝毫没有损害其分析的科学性。列宁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是的,我们平常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总是具体的,仰丈于任何抽象的和教条都不足以解决它们。
直到二十世纪中旬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知识”,是随着我们的创造性参与而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而不再是什么既成的,在任何时间、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如今我们所提倡的知识创新和素质教育都必须诉诸实践来理解知识,即要求我们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去空泛地恪守某种普遍有效的原则。人们同时也认识到,知识的主体也既不是单一的个体,更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性,而是特定时间和场合中具有连带关系的共同体。经历解释学或语用学转向的哲学则把主体性理解为主体间性,而文化学家们则更直接地在种族和文化群体的连带性(solidarity)意义上来解释主体性。用连带性来解释科学,科学家不是什么中立的、公正的代表,科学知识也不再以普遍有效性为前提。
在当代科学论中,地方性知识真正的始作俑者当数库恩。库恩不屑于去分析现成的和既有的知识,只关注知识实际生成和辩护的过程。通过“范式”这一“解释学的基础”,他告诉我们,任何科学共同体都带有历史的成见,因而都置身于一种局域的情境中了。重要的与其是分析普遍有效的方法,毋宁描述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中实际有效的范例。在他之后出现的“新科学哲学”(如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的社会构造论都试图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引伸,从正面来构造地方性的知识。
在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最好对当今时代知识观念的特征作几点确认。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知识在本质上不是一系列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而是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活动不只是在思维中进行,更主要的是在语言交往、实验,乃至日常生活中进行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探讨知识时就不可能不涉及到能力、素质与条件。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科学或知识理解为动词,即拉图尔所谓的“行动中的科学”。其次,科学或知识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并且自以为是的东西。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一起共同地构造了知识。知识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没有旁观者,而只有实际的参与者。“参与”(engaging)是表达“地方性知识”的一个关键词。由此可见,知识的主体必定是共同主体(“共同体”)。第三,既然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主体间性的问题,那么有效性的实现也必定诉诸于说服与劝导这样的论证与修辞手段,诉诸于认同、组织之类的社会学原理,并且也与权力这样的政治学问题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
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吉尔兹曾转引《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短文来告诉我们,究竟何谓“地方性知识”。文章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院的物理学教授,他在举了诸如一只标准的蚂蚁在一只标准膨胀的气球上之类的例子后,得出结论说:“物理学就像生活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也不会将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它的实质就是一个问题,或进而言之,即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和兴趣去投入进去。宇宙真是曲线做的么?这问题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和枯燥。理论不断出现又消失,理论并没有对与错,理论就像社会学的立场一样,当一些新的信息来了,它可以变化的。……物理学在迷惑;恰似生活本身如是这样也会容易陷入困惑一样。它只是一种人类活动,你应该去做出一种人性的判断并接受人本身的局限性。”[i]
二、知识的构造与情境
地方性知识的兴起无疑与康德对科学知识的先验构造,也与胡塞尔对严密科学的构想的失败有关。康德承认,科学知识本质上不再是分析命题,而是综合命题。对综合命题的奠基要求有逻辑以外的经验根据。然而在经验的条件下,尽管知识也可以是有效(Geltung)的,但是不足以保障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为此,我们必须预设某种“有效性”(Gültigkeit)的条件来保证知识“普遍认可的价值”(Anerkennungs Würdigkeit)。这些独立于经验来源的先天条件便构成了所谓的“先验主体”。胡塞尔的做法与康德不同。在反驳心理主义时,他要求我们把知识的实际生成过程与知识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区分开来。后者作为客观的观念是不受任何心理的和历史的因素所制约的,因而是绝对的。问题是,这种客观的和绝对的观念又是如何生成的呢?为了解释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必须还原到某种纯粹的意识结构中来。严密的科学知识只有在这种纯粹的生成结构中才能得以奠基。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其实胡塞尔本人在后期也意识到),这种纯粹的意识结构实际上并不纯粹,也许科学只有在更日常的“生活世界”才能寻找到自己的根据。另外,康德之后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作为先天的时空形式,甚至可以作经验的研究;任何范畴也都能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找到它的起因。与康德相比,胡塞尔更清醒地意识到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他已经听到了相对主义逼近的脚步声了。鉴于胡塞尔的告诫,二十世纪上旬主流的哲学家(如波普)与社会学家(如默顿)还依然恪守着这样的戒律:尽管我们可以用经验的、社会与文化的因素来描述构知识的生成过程,但是这与知识内容无关。但是这种戒律最后遭到库恩的摧毁。库恩发现,站在牛顿物理学的基点上根本无法判读亚氏物理学的价值。我们只能这样来解释,由于两者是依据不同的原则构造而成的,因此不能用牛顿的读法来解读亚里士多德。换句话说,知识的内容与准则只在特定时代的共同体内部得到辩护,因此也只对共同体成员有效。
如果库恩的说法成立,那么有效性问题只有置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中才有意义。或者就如同罗蒂所说,有效性与其说是客观性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连带性问题。连带性在人类学家眼里往往是一种种族关系,人们只能以自身所属的种族为中心获得判定知识的基准。然而扩展开来看,人们不只是由于血缘或地缘而产生连带,其实信仰、利益关系、观点和立场也均能产生连带感。基于连带性,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看待经济规律时,东亚与欧美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女权主义者,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在看待技术进步、环境和基因工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准则。
库恩的作法实际上把知识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纠合在一起了。他后来声称自己找到了一种同时又是内部史的外部史方法。依据这种方法,通过对社会文化史问题的研究同时可以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由于这一转变意义过于重大,他不得不谨慎处置。后期的库恩曾稍带犹疑地说,“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解释学基础,但它们本身并非是解释学的事业(hermeneutic enterprises)。”[ii] 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有着独立干情境解释的客观内容。与他相比,发端于爱丁堡的SSK则显得直言不讳。在布卢尔看来,既然有效性是一个主体间的问题,那么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也只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因素来加以构造。另外,在拉图尔、沃尔伽和卡龙等人看来,既然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就必须,也只能从当事者的当下活动出发,或者说是从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现场出发进行考察。鉴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特征,他们都自称为是社会构造论者。
A.皮克林在1992年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对SSK的近十年来的理论成果和内部争论作了系统的回顾与展望。沃尔伽在导言中指出:“在这一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新近的宣言中,这种传统已展示了一种相对主义形式的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现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的随机的产物。”[iii]
人们通常总以为,社会构造论是一种社会还原论,在方法上与胡塞尔批判过的心理主义没什么两样。这是误解。因为这样理解的社会构造论与其说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新型的本质主义。其实真正贯串于社会构造论的特征恰恰是“反思性”(reflexivity)。只有通过反思性,我们才能真正消除隐含在以往社会构造论方案中的社会实在论的幽灵。拉图尔和卡龙的“行为者网络”(actor network)方案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反思性。在这里,我们固然不能脱离社会因素来思考自然与技术,反过来说,离开自然和技术的社会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正是在这样一种由人、人造物和自然交错形成的复杂的网络中进行的。人们之所以误认为两者是可分离的,正是由于受到了技术决定论或者社会决定论观念的驱策所致。当他们把社会设定为终极的根据时,就把行为者网络投射到该点上去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以往,人们总是把研究的对象定位于自然-社会两极的位置上,其实,任何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和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一样都抽象的产物,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两极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与社会的“杂交物”(hybrids)。[iv] 可见,社会构造论决的宗旨并非是为既成的知识作出辩护,而是通过展示行为者网络情境的同时来构成知识的内容。他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与活动或实践无关的,或者与社会因素无关的知识内容。
在揭示科学家构造世界活动的理论框架中,他们把科学家、利益集团、以及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科学家、物质设施、以及自然现象(如微生物、海扇贝、潮汐、风等)之间的“技术的”关系置于同一层面上来进行考察。为了置身于这样的网络,科学家们还需要采用修辞的、乃至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权术来加入或组建成“不同族类的联盟体”,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持久的权力-知识的搭配模式。
在考察SSK时,有两个关键的论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创新决非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受到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因素制约的开放的过程。并且,对于科学而言,这些因素决非是某种外在的影响因素,而恰恰是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构成中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第二,对于科学、技术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人完全有理由根据其不同的用途给出不同的回答。真正的答案应该根据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争执、商议来作出。或者说,不同的解释之间的分歧与协合就构成了“科学”与“技术”这样的东西。宾奇把这样一种典型的社会构造论观点归结为“解释的可塑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v] 实际上,它意味着解释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
通过行为者网络来研究科学活动,与文化人类学家们所采用的“田野”方法最为相近。SSK实际上正是把科学家及其在实验室中的活动作为自己的“田野”。这一点在上,拉图尔和沃尔伽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构造》中对萨克生物学研究所中科研活动实情的描述,以及卡龙有关海扇养殖的报告最具代表性。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与沃尔伽以其亲身的经历向我们描述,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推进研究的,以及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研究活动中被构造出来的。他们试图证明,曾获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奎莱明和萨利两人关于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发现是一种社会的构造。书中他们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威尔逊和弗劳尔两位科学家之间的社会磋商过程,从而表明,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所从事的社会磋商,其实与发生在社会上其他人身上的种种日常的磋商,诸如政治的和商业的协商并无二致。萨克研究所的所长对拉图尔和沃尔格的研究方法十分欣赏。按他的理解这种方法是:“(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vi]
社会构造论者用实际构造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来告诉我们,只要介入科学知识生成过程作实地考察,我们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科学知识普遍有效的根据。卡龙和拉图尔曾明确承认,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自然科学的“祛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vii] 要弄清这一点,还须进一步探讨知识的辩护问题。
三、知识的叙事重构
依据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我们对知识的辩护只能伴随着知识的生成过程来进行,任何独立于生成过程的辩护都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辩护既是描述(叙事)、解释,也是论辩。S.图尔敏在《论辩的用途》中指出,作出解释就是发表观点,而发表观点则意味着一旦它受到怀疑和诘难,就需要作出辩护,用更充足、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它。这就叫“论辩”(argument)。历史上的论辩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基于事实根据的“论题的论辩”(topical arguments),二是基于逻辑根据的“形式的论辩”(formal arguments),三是基于论辩本身之必要条件的“元论辩”(meta-arguments)。与以往的演绎证明不同,康德在“先验演绎”中为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寻找到了一种“元论辩”的方式。后来,斯特劳逊把它引申为“先验论辩”(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近来兴起的亚里士多德热,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性知识的流行有关。如果说知识必须根植于科学的研究实践中,而不是被完全抽象化于表象理论中,并且理论只能在其使用中得以理解,而不是在它们与世界的静态相符(或不相符)中得以理解的话,那么对这样一种知识的辩护就既不可能用形式的论辩来证明,也不可能用先验的方式来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础。如果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那么对之的辩护也只能诉诸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论题的论辩”。反过来说也一样。由于这种论辩必须基于事实的根据,因此也是一种“叙事”。在前边提到的实验室研究中,当科学被作为实践活动来考察时,科学知识的构造中就已经包含叙事的成份在内了。科学家需要用自己的业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说服政府或企业财团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劝说和动员研究者来参与研究,还要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宣传、推销自己的成果,等等。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真理,而是在于动用一切修辞手段来营造出可信的情境,以说服别人。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性知识的观念。首先,“topica”原本也有“位置”的意思,表明论辩不是中立的,而是有立场的。当科学家们以具体的身份参与研究时,他不可能没有历史的负荷,不可能不带任何传统与成见。其次,叙事和事实的辩护反对方法,它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没有普遍适用的常规可循。包括一个人如何说话,如何倾听,如何达成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等等,都是如此。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实践智慧”(phronesis)这样一种行动的技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因为实践智慧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所以,一个没有普遍知识的人,有时比有普遍知识的人干得更出色。”[viii]
由于研究者受一定的利益关系支配,并且由于论辩各方的不对等地位,事实的辩护中必定包含了权力的因素。这与其说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不如说是科学政治学的范围的问题。J.劳斯认为,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叙事的区分,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政治学,即现代性政治学和后现代性政治学。科学知识起源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反对它们。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权力关系构成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找到了特殊的行为者和利益。福柯评论道,“权力必须被分析为一些循环的东西,或者宁可说,被分析为一些只有在链锁的形式运作的东西。它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在任何人的手中,决不适合作为日用品或财富。权力通过一个象网一样的组织而得以使用和行使。”[ix] 新实用主义者也告诉我们,权力与知识或真理具有内部联系,打开了科学实践领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揭示了真理的关系。从描述到介入与操纵,从知道什么到知道如何的转变,把我们引入了知识和权力的关联域,从而也引入了地方性知识,以及解释这种知识的科学的政治学中来了。
如今,有关地方性知识的叙事经常会遭受到一种两难的指责。你如果反对现代性的整体性(global)叙事,你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如果你拒绝接受为科学所讲述的合法化的故事,那么你就得接受相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方案。其实,如今作出第三种选择的大有人在。法因、哈金、卡特赖特、赫斯和劳斯等人都在主张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拒绝对相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作出让步。他们反对整体性叙事的理由很简单,即便这种合法化的努力失败了,或者压根就不存在这种合法化时,也看不出有任何严重的后果,科学技术照样迅猛发展。哈金的“实验实在论”强调,实验的进行依赖于实验室的地方性情境,并取决于实验所产生的预期效果。他认为,如果按下述方式理解的话,“现代性”还是可接受的,即“现代性”不是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确定的、普遍的情境,而是一个包含冲突的场所。在这里,之所以有潜在的认同正是为了使尖锐的实质的分歧成为可能。在哈金的意义上,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分歧,就成了现代性内部的分歧。
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一样,社会构造论方案其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科学知识构造出一套共同的社会解释的图式。当他们用新的教条来取代旧的教条时,SSK就背离了地方性知识的初衷,即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态度。由于每一种知识生成的情境总是具体的,因此不可能套用任何图式,即便是社会分析的图式也不例外。连贯做法只能是通过参与和介入,当事者(agent)根据科学活动实际进行来把握它的当下结构。
我们知道,参与和介入并非是对对象作客观的描述,因为参与者的介入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情境。或者说,对地方性情境的叙事始终意味着对它的重构。这也涉及到了学习与教育观念的转换。学习应该同时也是创新,因为学习者已经参与到重构科学知识的叙事情境的过程中来了。
四、地方性与开放性
地方性知识并未给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框定界限,相反,它为知识的流通、运用和交叉开启了广阔的空间。知识的地方性同时也意味着开放性。在地方性意义上,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工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正在途中(ongoing)。一种研究工作与其情境之间的叙事结构只有短暂的、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知识之所以会过时,是由于叙事结构发生了变迁。M.麦孔伯和布兰尼都试图揭示叙事情境所具有的意会(tacit)与易变(transient)的特性。“[科学家在其中理解自己的工作的]情境总是被重组和更新的。要是我们刻意去寻找它是找不到的,因为它不断地扩张着、变迁着、被改造着。个体发现的意义来源,及其有效性的基础仍然处在我们的把握之外。然而这却是为每一工作中的科学家们所熟知的情境;它在科学家中已‘人尽皆知’。”[x]劳斯则进一步强调说,科学叙事的构造始终是一个“持续重构”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地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叙事情境。”[xi]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曾力图用语言的用法来取代语言的意义。离开用法谈何意义?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同样的道理,时过境迁,一种知识不见得是错了但是却没用了。因为用法变了。也许有人会说,且慢,科学知识的内容是无时间性的。胡塞尔就曾争辩道: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便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也是真理,尽管他们尚未发现,也无法理解这一定律。很显然,胡塞尔并不理解知识的构造应包含叙事的成份,以及用法在内。
当然叙事也要求连贯,只是不是作为表象的连贯,而是作为实践的连贯;不是作为命题的连贯,而是作为情境的连贯。麦金泰尔在《追求德性》一书的开篇就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设想在一次普遍发生的骚乱中,实验室、科学家和图书设施一并被毁……。许多年后,人们试图恢复早已被遗忘了的自然科学,但是从残留下来的文字中,已经无人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为那合乎具有稳固性和连贯性的一定准则的言行和那些使他们的言行具有意义的必要的背景条件都已丧失,而且也许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xii] 事实上,由于启蒙的分裂,一种统一的、普遍性的叙事已宣告失败。于是麦金泰尔断言:“主观主义的科学理论将会出现”。这时,哲学的分析,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的分析都将无助于我们。因为这种分析都要求以某种普遍的概念图式和纯粹的意向结构为前提。其实当“生活形式”转换了,你再怎么努力去拼凑回原来的知识内容也无济于事。
要说地方性知识必定会否定科学知识中具有独立于叙事情境和用法的确定内容,那不是事实。它只是告诉我们,离开特定的情境和用法,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便无法得到确认。如今的高等教育经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学生还尚未跨出校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就已经过时了。当然不是说它们错了。一种明智的培养目标,与其是让学生掌握多少确定为真的知识,不如让他们掌握重构科学叙事的能力。他们必须学会改变原有的知识以适应新的情境的方法。劳斯主张说,最好先别去考虑一种想法怎样才是正确的,能否得到证实,而是考察在何种情境条件下这种想法才具有科学的意义。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基本,但是却更容易为传统的知识观念所忽视。并非所有有关自然世界的真理都具有科学意义,都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除非我们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区分什么是值得去知道,值得去做,值得运用,值得考虑的,什么是无关紧要,无用的和无意义的,否则我们将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xiii]
“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在空间上的封闭。地方性情境是可以改变、扩展的,当然不是扩展为“普遍”,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罗蒂认为,他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绝非与世隔绝,而恰恰开启了一种对话的空间。塞蒂纳的实验室理论也不例外,她指出:“在这种[交流与交往]状态下的实验室是生活世界的聚焦点,就单个实验室而言都是地方的,但是它又能远远地超越单个实验室所给定的界限。”[xiv] 即便哈贝马斯也承认,现实的交往共同体总是“地方的”,受局域性条件制限的,有时甚至受到意识形态的扭曲。所谓普遍的有效性与其说是某种事实,不如说是包含在知识中的一种潜在的“要求”。科学知识总是“要求”获得他人的认可,并取得共识。为此,它们必须被置于实际的交往过程中去才能得到“验证”(einlösen)。换句话说,科学叙事总是“共同叙事”(common 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一起共同构成叙事的情境,也一起共享这个情境。
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与塞蒂纳在《知识的生产》(1981)中都曾以科学论文的写作为线索,表达了科学叙事的开放性。科学论文当然是写给读者看的,于是读者便被纳入了共同叙事的结构中来了。当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引文注释时,并非想表明自己的研究是多么“专业”,而是试图吸引读者来参与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个台阶。科学研究的情境也就随着阅读中互动的深化与扩展而得到不断的重构。一种研究如果不能成为进一步扩展的研究的动力,就会丧失其科学的意义,也就不再能吸引读者来参与。
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劳斯的观点:“在科学中,合理接受的标准不是个人化的,而是社会化的,它们体现在体制中。”“科学观点是建立在一个修辞空间,而不是逻辑空间中的。科学论点其实是对同事进行理性的劝导,而不是独立于情境的真理。”[xv]
地方性知识非但不排除,而是恰恰以竞争性理论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对传统的挑战,实际上都是对的情境的矫正,乃至贡献。理论的竞争并非如默顿学派理解的那样,是为了得到奖励和专利,更主要的是为了主导在未来研究中的方向和地位。当然,结果不是哪一方的一相情愿,而是通过协力交互地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知识非但不排斥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而恰恰是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与起点。
参考文献
1.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219-220页。
2. Kuhn,T.S.: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David R.Hiley(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Science,Culture, Cornell Uni.Press,1991,p.23.
3, 7, 14, Pickering(eds):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Press,1992, p.1, p.358, p.129.
4. Callon,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Brieuc Bay,in:J.Law(eds):Power,Action,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1986,pp.200-201.
5. Pinch,T.J./Bijker,W.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i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 MIT Press, 1987, p.40.
6. Latour,B./Woolgar,S.: Laboratory Life, Princeton, 1979, p.12.
8.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1141b15.
9. Foucault,M: Power/Knowledge, New York:Pantheon, 1980, p.98.
10. Macomber,W: The Anatomy of Disollusion, Northwestern Uni.Press, 1968, p.201.
11, 13, Rouse,J.: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Inquiry,Vol.33,1990, p.181, p.186.
12.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5. Rouse,J.: Kno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Cornell Uni.Press, 1987, p.120.
“科玄之战”百年反思
盛晓明
[摘 要]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华彩一章,中国人自维新变法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地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在此后的近百年间,论战双方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复重现,上演了诸如“两种文化”与“科学战争”的论战。然而,启蒙的逻辑并未协调好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也缺乏基本的历史意识。事实上,科学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在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对科学及其功能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价值冲突尚在,诸如此类的论战还会改头换面地发生。
[关键词]科玄之战;启蒙;“两种文化”;“科学大战”;后学院科学
一、论战的景观
在新文化运动的画卷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玄之战”)无疑是出彩的一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初来乍到的“赛先生”举办的一场“见面礼”(胡适)。论战实际上是由访欧回来的梁启超点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重创,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纷纷进行反思,认为战争给世人带来的不仅是“欧洲科学的危机”,更是“欧洲人的危机”(胡塞尔)。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多少受到了欧洲悲观主义情绪的感染,认为自己从欧洲一片萧瑟中见证了“科学万能”的破产,“赛先生”没能拯救欧洲人,也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书中第一章有这样一段描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
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
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1]57当时,包括张君劢在内的访欧团成员多少都感染了这种情绪,他们的反思中有两点认识是共同的,首先,科学不能,也不应该涉入人的精神和价值领域,不然就会重蹈一战的灾难;其次,西洋文明有自身的弱点,不足以取代本土文化的地位。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演讲中明确指出,“人生观问题的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2]35。这类话听起来并无过错,但在当时恰恰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国人尚未与新来的“赛先生”行过“见面礼”,这厢就开始揭短了。对此,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们尤其愤怒。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就指责是不是“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了。在“科玄之战”中,“玄学鬼”成了所谓“反科学”一方的代名词。当时,支持科学一方的还有化学家任鸿隽、心理学家唐钺、教育家吴稚晖,以及胡适、陈独秀、瞿秋白
等,支持玄学的一方主要有张东荪、林宰平。卷入论战的名人、学者还有张申府、朱经农、孙伏园、王星拱、陆志伟、范寿康等。
科学一方在论战中明显处于优势。不错,启蒙就是要矫枉,而矫枉必须过正。在他们看来,只有将“赛先生”提升至宗教信仰的地位,方能驱逐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因此,如何传播科学精神,并在知识论和价值论上提升科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当务之急。在中国文化中,争夺正统的地位历来是性命攸关之事,免不了心浮气躁,火药味十足。撇开那些激烈的言辞不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中即公允地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3]151其实梁启超也并不认为科学已经“破产”了,只不过它不再是“万能的”了。科学无疑能带来物质财富,但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与关怀。胡适强调的则是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科学的赐福,就谈不上它所带来的“灾难”。这时候去奢谈负面效应其实是无病呻吟,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他的意思很明白,只有优先发展科学了,才有权谈论科学中存在的问题。再说,即便科学出了问题,也不可能通过玄学,而只能通过科学自身的进步来加以解决。
可见,这场争论本质上是两种逻辑、两种态度———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争执,这种争执最初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经过20世纪的发酵,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当下。本文不打算具体地描述“科玄之战”的过程,而是想追问,诸如此类的论战为何在一百年间不断重复发生,以及各种论战都有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与后续效应。首先我们注意到,“科玄之战”实质上是关于文化正统性的较量。由于“赛先生”还刚刚进入中
国,要想取代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来完成启蒙的任务,对科学的神圣化和对传统的激烈批判都是必要的。但这也给百年中国的文化留下一项未完成的工作,即作为批判武器的科学,其自身是否也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从欧洲的视野看,始于康德的思想革命多少修补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缺陷,但对于当时极其落后的中国和混沌不堪的文化状况来说,以欧洲为标准是难以企及的。哲学家阿佩尔曾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难点:
这些非欧洲文化已经并且还将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技术工业生活方式及其科学基础,它们被迫与自身造成间距,被迫与它们的传统相疏远,其彻底程度远胜于我们。它们绝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解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去的断裂。[4]70-71
其次,如果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是有限的,那么它能否与人文知识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呢?答案本来是最清楚不过的,但一经牵涉文化的正统性问题,并且关系到民族国家命运的抉择,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即便优雅的学者也很难心平气和。“科玄之战”以来的近百年间,诸如此类的论战之所以在不同的时间和国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除了上述因素外,还与学科偏好、职业利益纠缠在一起,从而显得更迷离,更吊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59年斯诺(C.P.Snow,1905-1980)挑起的“两种文化”的论战、发生在20世界末的“科学战争”以及21世纪初发生在我国的“科学”与“反科学”之争,等等。本文认为,如果说这些论战都受制于某种共同机制的话,那就是启蒙的逻辑。启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事业,但启蒙逻辑却是不连贯的,甚至是断裂的。自然的法则与生活世界的自由原本就受制于不同的逻辑,就如同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责问的那样,如果非要把精神性的东西都归咎于自然法则,我们将何以安放自己的道德良知?从这个角度看,陈独秀和胡适他们对启蒙的理解不无偏颇之处,我们固然通过科学来达成启蒙的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科学的认知目标来取代启蒙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处理相对谨慎一些,他并未把启蒙简单地归结为科学或民主的价值。启蒙是一种更基本且深层的要求,即通过自身理智
的自觉或觉醒达成的“自主”状态。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共同体,还是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如此。如果把启蒙局限于某种具体目标,必定会导致启蒙的分裂。这正是引发上述一系列论战原因之所在。
再次,在库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是一种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它也在演化着,不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追踪百年来的历程,科学的确经历了一个由“归圣”到“还俗”的过程。陈独秀的工作和19世纪40年代惠威尔(W.Whewell,1794-1866)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将科学“归圣”。惠威尔以圣经中不同的圣徒为原型来写科学家的传记,而陈独秀则直接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值得我们去信仰的“宗教”。的确,在传统观念的控制力日渐式微的社会里,世人需要新的“救世主”,为了“救亡”,也为了“解放”。然而,梁启超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没有错,一战中以及战后的欧洲科学的确出了问题。问题的实质就在于科学“还俗”了,至少不像19世纪的思想家想象的那样神圣。表现之一:实证主义的兴起,它在崇尚科学的同时也把科学工具化了。表现之二:“纯科学”的理想和科学“自治”体制受到侵害,科学活动和政府(军方)产业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苏联在科学上的成功、贝尔纳主义的兴起以及二战后各 OECD 国家对“创新”的关注都加速了“还俗”的过程。如今,科学的启蒙任务已告完成,它已渗透到了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质疑科学呢?原因上文已经有所交代,就一个人、一个共同体或者一个民族所要达到的自觉与自主而言,启蒙还在途中。因此,“玄学鬼”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地驱逐掉,它始终伴随着我们对进步和发展的反思。也许科学和玄学是互为镜像的,离开对方就无法有效地反思自身。
二、启蒙的逻辑
欧洲的思想启蒙在法国发生,却是在德国完成的。法国的启蒙主义者通常只是以科学为武器来完成其反传统的事业,却不深究科学活动本身的条件及其界限。这样很容易陷入唯科学主义,用一种新的独断来取代宗教的独断。在康德看来,实现人类理性的自我批判,科学首先要成为批判的对象,要谨慎地审视其基础,看其是否足够牢靠。这意味着科学自身的正当性仍然是一个问题,需要重新奠基。康德发现,无论是休谟式的自然主义,还是法国启蒙学者的自然主义都是成问题的。的确,科学离不开来自经验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必须受到理性自身法则的规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两个批判性的论断值得引起我们注意。首先,数学与自然科学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因为它们可以同时满足经验性与先天性两方面的条件。然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却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性的证据可以支持其超验的陈述。这个论断很重要,从这里出发,引发了新康德主义者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其次,虽说形而上学在科学领域中丧失了合法性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实践理性领域中也同样如此。恰恰相反,离开形而上学,我们将无从设想人类的任何道德命令。对康德来说,人同时是两个世界的公民。在现象世界,科学的规律支配着一切,也包括人自身;在本体世界,人只受制于自由的法则。康德的结论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启蒙的逻辑,但却颇具远见。按照他的说法,“我限制科学,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
用康德的论断来评判“科玄之战”是饶有兴味的。他的前一个论断支持了科学一方,因为形而上学在现象世界中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但他的后一个论断似乎又是支持玄学一方的,因为人生观问题受制于自由的法则,的确超越了科学所能企及的边界。人类理性原本就是包容的,在认知上可以依据自然的法则,在实践上则可以遵循自由的法则,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并不构成直接的冲突。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科玄之战”还有打下去的必要吗?
然而,康德其实并未如愿地调和了矛盾,相反,他对现象与本体,自然与自由的划分为日后一系列更大的争论和冲突埋下了导火索。在他那里,人类理性的根据毕竟是不统一的,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即便动用了体系的建筑术也无法修补这个裂痕。在他之后,叔本华、尼采他们可以从自由意志出发去消解科学的因果必然性,而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则加速滑向了唯科学主义。于是,原本隐藏在人内心的两种希腊式的倾向即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由于受到某些因素,如信仰、学科偏好或职业利益的触发,很容易外化为两种对立的立场,乃至上升为哲学上的党性原则。
之所以会这样,多少也与现代性和启蒙主义对科学进步的偏执有关。按照孔多塞的说法,迄今为止,宗教和形而上学所要解答的一切问题,要么变成了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要么就是假问题,在客观上销声匿迹了。陈独秀也有诸如此类的说法:“……地球之成立、发达,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学法则说明之……一切动物,有最下级单细胞之动物,以至最高级有脑神经之人类,其间进化之迹,历历可考……无一逃于科学的法则耶?”[5]551
另外,在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其代表人物所采用的基本策略也出奇地一致,即首先通过二分法区分出“科学的”或者“非科学的”、“反科学的”;然后再将后者置于进步的对立面,并作为不正当的东西予以放逐。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是没有分别的。孔多塞给出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起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大凡启蒙主义者都是唯科学主义者。
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一书的开篇中就指出: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种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简言之,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普遍推广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6]1
郭颖颐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陈独秀,也包括胡适。他们都不是科学家,也未曾从事过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可见,唯科学主义与学科偏好、职业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只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宗教。和我国当时的情况不同,早在19世纪下旬的英国,科学的职业化已经完成,但这个过程显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也经历过一场激烈的论战。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认知的权威主要还由教会拥有,自然科学尚未把自然的最终真理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关于自然,科学家提供了一种世俗的、非人格化的图景,谈论真理是把持着大学的神学家们所从事的工作,自然科学的从业者们只需
置身于类似于作坊的实验室中,埋头做具体的发明和解释工作。可是一场大规模的论战扭转了这个局面。在回顾这场论战时,弗兰克·特纳(Frank M.Turner,1944-2010)的观点颇具新意。在
一篇题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维多利亚式论战的职业因素》(1978)的长文中[7],特纳指出,这场论战一开始就不是思想与认知的冲突,而是一场职业及其话语权的冲突。一开始时,新组织起来的学者共同体并没有觉得自己在自然哲学上的立场与基督教神学有任何分歧,只是职业习惯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差异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除了少数激进的好战分子试图用不可知论来对抗教义外,多数都认为自己的工作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神学在自然界中的作用。那么为何产生冲突呢?答案是,为了行业的利益。科学家一经形成了共同体的自觉,自然需要寻求职位、社会地位、财政支助以及正当的话语权,当他们发现这些社会资源大部分都被神职人员所垄断,或者至少受到神学的制约时,竞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当时,科学家一方采取的竞争策略和后来胡适的策略如出一辙,都是“科学的自然主义”。这种策略坚持一切知识均应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合法性的策略。这种策略不仅向人们展示了科学方法对自然现象做出预见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出了一种知识主张究竟是否有效的基准,没有给信仰乃至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留下任何空间。即使到了19世纪,疾病的蔓延、作物歉收、自然灾害依然被神学家们解释为神对人类作孽的一种惩罚,解决的办法自然是信奉教会的道德说教,或者请神父去为受灾或患病的人做祈祷。科学家们则告诉民众,心灵的祈祷、上帝的意愿和自然现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甚至从统计分析中也找不出任何有效的证据。相反,诉诸科学来预测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有据可查的。
事实上,要想有效地抵御一种权威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另一种权威。到19世纪末,神职人员逐渐退出了争论,他们的行业利益也受到损害。至少在大学与学术机构的职位上,神职人员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呈明显下降的趋势。相反,科学的各门学科快速发展,其中应用性的、技术性的知识门类的扩张速度最为显著。这场论战无疑促进了“职业专家”在身份上的自觉,同时也提升了职业团体的共同体意识。
与这场论战相比,斯诺挑起“两种文化”的论战就其动因而言有点奇怪,似乎与职业利益无关,也许只能归因于学科偏好。1959年,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斯诺本人既是物理学家,也是小说家,因此能敏锐地捕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存在。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紧张乃至敌对状态。通常情况下,两个阵营中的人彼此鄙视,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甚至都试图在价值上放逐对方。不过,斯诺的立场看来也不是中立的,他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大都是天生的卢德派,对未来缺少信心,不仅在政治上愚蠢,而且不怀好意。他举证说,从1914年到1950年,百分之九十的著名人文学者都是如此。相比之下,科学文化更加乐观向上。至少科学已经成为提升社会福祉的有效途径,因而可以充当价值的仲裁者,并有理由去放逐人文文化。
我们不得不说,斯诺的观察是敏锐的。只是他的结论非但不能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裂痕,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对立。其实在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论题的7年前,哈耶克就已经出版了他的名著《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认为科学由于自身过度的权威而充满傲慢与偏见。一个缺乏历史、文学和艺术素养的头脑是不可能形成健全的人格的,因此,相信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唯科学主义”者,同样也不可能成为有杰出成果的科学家。当时,与斯诺对垒的主角是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他认为,斯诺对两种文化的划分迎合了公众默认的低下标准和口味。“人文学者”、“人文文化”和“传统文化”这些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斯诺并没有交代清楚,这样就很容易把整个传统文化置于“反科学”或“非科学”的位置上。
这场争论引发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哲学上看,它把历史主义者置于自然主义者的对立面,也引发实在论者把建构论者当作对科学不怀好意的卢德派加以围剿,从而将原本是隐晦的学术分歧变为公开的文化冲突。
到了20世纪末,按理说历史能够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裂隙。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两种文化之间陷入了更深的对抗之中。随着“后现代科学”兴起,人文文化试图一改以往的守势与边缘状态,
向作为主流的科学文化发起挑战,引发了一场所谓的“科学战争”。
1994年,美国的生物学家格劳斯(P.R.Gross)与数学家莱维特(N.Levitt)合著的《高度的迷信》一书首先向“科学的批判”发起反批判。作者的语言很煽情,表面上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科
学”、“非理性”倾向,实质上暗含了对库恩之后的科学论的全盘否定。这时,作为左翼阵营的刊物《社会文本》随后组织起一期名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s)的特刊予以反击。
1996年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给这场“战争”增添了不少戏剧色彩。物理学家索卡尔(A.Sokal)故意歪曲了一些物理学理论并修改了数据,假装成后现代科学的支持者杜撰了一篇题为《跨越边界:走向量子重力论的解释学》的论文,投稿到《社会文本》,并刊登了出来。随后,索卡尔主动披露原委,玩了后现代科学一把。索卡尔的玩笑开大了,引起媒体与公众一片哗然。为了加重火药味,他为1998年出版的《流行的谎言》一书加了一个副题:《后现代文人对科学的滥用》。无论是拉康、利奥塔,还是奎因、拉图尔都成为他数落的对象。索卡尔的策略实际上是以攻为守,其底线是把持住共同体的“自治”原则,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科学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事,外行的说三道四都歪曲了科学的本意。很显然,他把自己置于科学原教旨主义立场上了。
直到2000年,这场“战争”才悄然降下帷幕。通过“战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同样不容否定的是,科学又是一项公共的事业,它的活力与生命力就在于公开接纳不同文化群体的参与、反思乃至批判。在这场论战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乃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背景上看,后“冷战”时代,科技政策的转型与资源的重组导致了科学和人文两大阵营为争夺社会资源和话语主导权的竞争表面化,甚至白热化。“科学战争”发生 的 前一年,克 林顿政府 已 经取消了耗资10000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并终止了德州已完成五分之一、耗资110亿美元的超导对撞机计划(SSC),致 使 大 批 科 技 从 业 人 员 得 不 到 科 研 经 费,甚 至 失 业。 用 法 国 科 学 人 类 学 家 拉 图 尔(B.Latour)的话说,“一小撮物理学家”为争夺巨额 R&D 经费编造了“一种新威胁”,认为不是政府,而恰恰是一批来自外国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坏了他们的好事。
到了21世纪,一场类似的“科学战争”又紧接着上演了,只是场所不在美国,而是转换到了国内。不过,与“科学战争”相比,它更接近于20世纪初的那场“科玄之战”。在2004年北京召开的“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教授的演讲被当时的媒体炒作成杨教授向《易经》“开火”,认为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如果说90年前的“科玄之战”起因于玄学家去挠科学家的痒痒,那么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杨振宁的说法引来了中国哲学界和易学界的强烈反弹与批评,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的一批学者甚至发表了《致杨振宁教授的公开信》。很快,讨论从国内扩展到了海外,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在一片叫骂和讨伐声中,有的院士站到杨振宁教授一方,指责《易经》只是一种“笼统思维”,受此影响的中医同样也是过时落后的,云云。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论战把学界搅得昏天黑地。在这场论战中,媒体的炒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杨振宁被公开问及“炮轰”《易经》的问题时表示,其实他八成是肯定《易经》的,只有两成是指出它的负面作用。人们常说,真理会越辩越明,其实不然。当科学问题伴随着意识形态、信仰、学科偏好乃至职业利益时,各种论战往往会扯开愈合了的创口,情绪越辩越亢奋,论调越来越极端,结论也越来越诡异。结局都一样,不了了之,回归平静。
三、从“归圣”到“还俗”
启蒙的逻辑还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历史意识阙如。正如库恩指出的那样,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学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辉格史”,即用胜者的逻辑去评判发生过的一切。启蒙主义者创造了那种曾使人误入歧途的阅读原著的方式,而他们自己也常陷入这种误读之中。在库恩眼里,本-大卫(J.Ben-David)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1971)就属于“误读”的那一类。作者把欧洲19世纪以后形成的现代科学家的角色原原本本地套用到17世纪的英格兰、18世纪的法兰西,乃至古希腊中去。这种本质上乃非历史的观念导致了科学概念的发展与制度史的社会结构的分离。库恩在《科学的增长:对本-大卫‘科学家的角色’的反思》(1972)一文中指出,当本-大卫把现代欧洲科学家的角色扩展到整个历史过程,并作为社会普遍现象时,他的论述有一个前提,即“科学”这种东西似乎永远都是现在时的,独立自存的,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8]。
科学的确在变化,只是不像库恩所说的那样,通过范式的转换(科学革命),由一种常规科学转换到另一种常规科学,而是由常规科学一下子跳到了“后常规科学”,或者说是“后学院科学”。使用“后”这个概念需要谨慎些,一不小心又会掉进争议的怪圈。不过,无论我们基于哪个学科,即便是一个局外人,也都能感受到科学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冲击。
一是“大科学”的诞生。从一战开始,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政府(或军方)动用巨额经费来组建大平台,强势地介入了科学活动,并主导了研究议程的设置,同时也就挤压了“自治”原则在科学共同体中的适用空间。不仅普朗克所创导的“纯科学”成为泡影,布兰尼所要求的科学的“治外法权”也成了乌托邦。
二是“产业科学”的涌现。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有过“培根的科学”的提法,只是没做深入的考察。拉维兹(J.R.Revez)在他的成名作《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1971)中曾明确界定了“产业科
学”的概念。产业实验室、政府政策咨询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的涌现以及产、学、研的一体化,打破了科学与产业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甚至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边界,要求按市场法则来重构科学体制。
三是各种跨学科研究模式的展开。各种形式的多学科协同研究、交叉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突破了以学科为母体的制度设计,既有的方法论规范对跨界成员来说丧失了规范性的力量,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甚至处于“失范”状态。
上述变化都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就意味着科学文化所面对的“他者”不再是什么“玄学鬼”或者“居心叵测”的人文学者了,而是另外两个更强大的“他者”,即政府(包括军方)和产业界。他们携带着更强大的世俗价值、资金和社会动员力量,以“创新”的名义颠覆了科学既有的价值和精神,当然也打破了科学的“自治”疆域。
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科学经历了一个“归圣”的过程,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又悄悄地踏上了“还俗”之途。“归圣”的工作可以从惠威尔撰写的科学家传记中一见端倪。惠威尔是一名牧师和矿物学教授,更主要的是,他还向世人讲述了法拉第和达尔文等科学家的故事。他的描述有些类似圣经中的故事,也许他就是以圣经故事中的圣徒为原型来塑造科学家形象的。即便时至今日,经典的科学家形象依然是圣徒式的、踽踽独行的理智探险者。另外,惠威尔还把盛行于中世纪行会的自律和自治体制套用到科学家群体中来。事实表明,这种方式成了后来科学史的主流,自治的感觉随着科学形象的确立而一并得到史学家甚至是哲学家们的认同。自治体制的核心依然是科学的目标问题,科学研究的目标不为别的,只为科学自身,比如科学家的兴趣或好奇心。一旦研究者必须在项目设计中交代清楚与普罗大众的关系,以及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时,自治体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其实,“归圣”的过程中就已经隐含了“还俗”的因素。20世纪初,实证主义的盛行对专家统治型社会的理念进行了确认。不过,科学一方在竞争策略上的胜利也包含一种导致自我否定的危险。首先,科学在认识与理智上的权威必须向工具性、技术性的方向转移。凭借工具性的效用,科学在与宗教、传统文化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如今它也只有放弃目的理性上的追求,任凭工具理性在科学中蔓延,直至最后把自己蚕食而尽。德国的化学家们在一战中的表现以及物理学家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其次,科学一经被工具理性所占据,势必导致它对外部权威尤其是政治权威的依赖。迄今为止,尽管政治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科学的权威,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至少还存在着一种由科学权威向政治权威转化的可能性。只要科学的重心依然是技术与效用的话,上述可能性将很快演变成一种不可抵御的且不可逆转的趋势。
科学的演变似乎印证了贝尔纳的理论。贝尔纳不屑于科学“自治”之类的神话。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需要,只要略懂科学史的人都知道,促进科学发现的动力和物质手段都来自人们对物质的需求。科学之所以在社会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完全是由于它对提高经济效益所做的贡献,而不是受崇高的目标驱使。只要终止产业界和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助,科学的地位很快就会沦落到中世纪的水平上去。毋庸否认,这位英国结构物理学家在政治倾向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立场上则是激进的工具主义者。
竺可桢,这位胡适早年的同窗、用“求是”来演绎科学精神的浙江大学校长,在阅读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并拜会了贝尔纳后,几乎成了贝尔纳主义者。当他在莫斯科见证了“大科学”的成效后,脑海里已经酝酿成熟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政策的基本框架。吊诡的是,二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首脑和知识精英们在经济政策上都崇尚自由主义,而在科技政策上却都成了贝尔纳主义者。只是他们撇开了贝尔纳主义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分,而把关于高效发展的计划、规划、人力资源、资金和设备等想法作为制定科技政策的合法性根据。
从职业化科学诞生的第一天起,科学家们就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边界与纯洁性将有遭受侵害的危险,并尝试用“自治”的策略去化解。他们一开始面临的“他者”是神学,但到了20世纪初,宗教显然已不再对科学构成威胁了,接着又设法清除另一个“他者”,即心怀叵测的人文学者。但科学并未迎来唯我独尊的时代,而是需要应对政治和产业这两个更强大的“他者”。这时,科学家共同体的抉择是矛盾的,既要自主地存在,又需要外部提供资助、保护;既满足了客户的要求,又拥有好奇心得到满足后的快感。总之,既供奉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上帝”,即对真理的追求,又不能让外部的“恺撒”失望,即服务于现实中的产业、政府甚至军方的需求。
其实,分裂已经在所难免。一部分科学家,像索卡尔那样的物理学家,更愿意留在“圣坛”上。
他们的“自治”策略也变得更加保守,让外界尽量别去触碰这块“净土”。当年,韦伯在谈及神圣化时就曾讨论过“密室效应”。有些人曾通过与外界的隔绝来维系自身的神秘感、神圣感,问题是,“净土”已不在了。
更多的科学家则跳出了“密室”,设法在政府与科学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一点上,斯诺和后来的索卡尔他们不同,在斯诺看来,科学不应该陷入与“他者”无休止的论争,而应该让政界、产业界乃至人文学者更多地掌握并理解科学,同时也应该让科学研究人员走出去,去掌控政界与产业界。在挑起“两种文化”争论的5年之前,斯诺就写过一本书,名叫《新人》(The New Man)。“新人”指的就是这批新型的知识精英,他们具有管理基金会、实验室、学术机构的经验,能招募从业者参与大型的科学工程,代表科学家游说军队和政府官员,甚至与产业界人士磋商。他们集学术文化的专业抱负与政治抱负于一身,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方式,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寄托了斯诺对解决“两种文化”冲突的期望。
从20世纪之初在落后的中国爆发的“科玄之战”,到20世纪末在先进的美国爆发的“科学战争”,论战双方的攻守已经发生易位。在当时的中国,科学一方代表革命与激进思想,玄学一方代表了文化的保守势力;而在20世纪末的美国,科学的一方代表文化的保守势力,对方则代表了激进思想。原来作为“反科学”一方的人文学者更能接受“大科学”与“产业科学”所带来的“创新”局面,而当年作为进步之象征的科学一方如今却无视科学活动的任何变化。正如“后学院科学”概念的提出者拉维兹所说的那样:
有些人不满这种新的实际活动也叫科学。但科学从古至今都在不断地演化着,以应对将来改变了的人文需要,它还将进一步演变下去。我们有必要拓展科学传统解决问题的策略,深化对它们的哲学反思,并扎根于体制的、社会的和教育的境况,以解决这种基于科学的产业文明给我们造成的问题。一看到科学内在的不确定性就觉得不舒服的人,其实是留恋那个安全、简单却一去不复返了的世界。[9]255
时过境迁,现今扮演浪漫主义角色,带着几分留恋、怀旧、伤感的人,已不再是德国的魏玛文人,不再是中国的玄学家,也不再是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而可能是占据科学核心地位数世纪的物理学家了。对那些已经适应了自由研究,并把学术视为自己全部生活的研究者来说,他们正在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乐园”。
苏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卡比萨(P.L.Kapitsa)在回顾与卢瑟福在一起的日子后掩饰不住自己的伤感:“在卢瑟福去世的那一年(1938年),那段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曾给年轻时的我们带来过无穷欢乐的幸福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现在已失去了自由,科学已成为生产力……如果卢瑟福还在世的话,会不会拿这事当个玩笑开,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呢?我不知道。”[10]725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Liang Qichao,Travels of
Liang Qichao:Travels in Europe & Travels in New Continent,Shanghai:Orient Publishing House,2006.]
[2]张君劢:《人生 观》,见 张 君 劢 等:《科 学 与 人 生 观》,济 南: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1997年,第 33-40页。[Zhang
Junmai,″Philosophy,″in Zhang Junmai et al.,Science and Philosophy,Jinan: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7,pp.33-40.]
[3]胡适:《胡适文 存》卷 三,北 京:外 文 出 版 社,2013 年。[Hu Shi,Collection of Hu Shi:Vol.3,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13.]
[4][德]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K.O.Apel,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trans.by Sun Zhouxing & Lu Xinghua,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7.]
[5]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Chen Duxiu,Collection of Chen Duxiu,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7.]
[6][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900—1950)》,南京: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1989 年。[D.W.
Kwok,Scientism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anjing: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9.]
[7]F.M.Turner,″The Victorian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A Professional Dimension,″Isis,No.69
(1978),pp.356-376.
[8]T.S.Kuhn,″Scientific Growth:Reflections on Ben-Davids′Scientific Role′,″ Minerva,Vol.10,No.1
(1972),pp.166-178.
[9] S.O.Funtowicz & J.R.Revez,″Three Types of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normal Science,″in S.Krimky & D.Golding(eds.),Social Theories of Risk,Westport:
Praeger,1992,pp.251-273.
[10]V.K.McElheny,″Kapitsas Visit to England,″Science,No.153(1966),pp.725-727.
4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6卷”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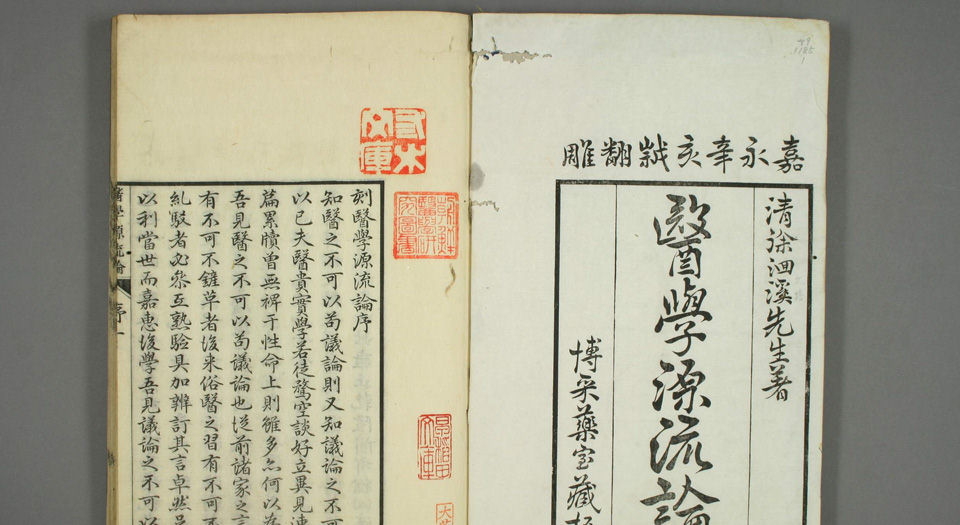
评论0